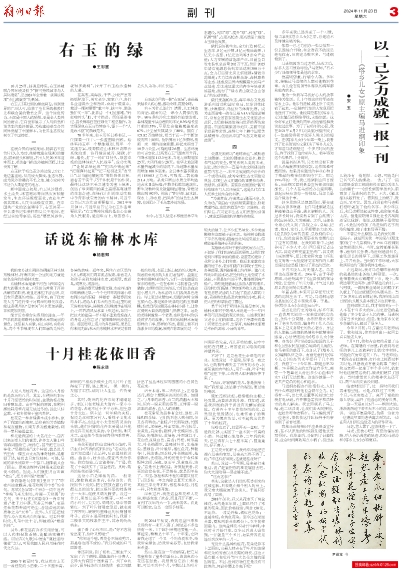以一己之力成就一报一刊
文章字数:2346
●安玉
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当拿到《塔乡儿女》之后,总是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。
依靠一己之力创办一张县报和一份县级综合刊物,在全省我不敢说是绝无仅有,但肯定为数不多。马进纲做到了。
马进纲因为当过老师,从政之后,好多人还习惯称呼他:“马老师。”有不少厅处级领导都是他的学生。
德高则望重,行端令人敬。多年来,接触过马进纲的人都对他特别尊重。有几位省级领导和部队的将军都和他有联系。
他为一位将军寻找好心人的故事被传为佳话。几十年前这位将军还在家乡上学。他步行进城,路上肚子突然痛了起来,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发现后把他送到了医院。他说曾经委托《塔乡儿女》主编马进纲给寻找,未能如愿。这位将军正好是我的同学,他也曾经和我谈起过此事。为了了却将军的心愿,我在2021年6月7日《应县报》头版刊发了《一位高级将领寻找好人陈义》的短文。在《塔乡儿女》今年第一期上,我看到了社长贺诚的文章《为了塔乡儿女》,才知道马进纲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查访,终于找到了这位骑车人。将军得知这个结果后,十分高兴。
说是县报县刊,其实并没有正常的人员编制和财政拨款,运作困难可想而知。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很难坚持下去。那是1996年的一天,我已经调到山西日报社,马进纲又回到县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。几个人在马部长办公室闲聊,说起应县应该办一份报纸,马部长最适合做这个事。
好多思路只是想想而已,要变成现实有诸多难题。也许马进纲就是这种能够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人。没过多长时间,我突然看到了白纸黑字的《应县报》,大为震撼。之后,马部长全身心投入到了办报之中,总编、记者、校对、发行,几乎都要亲力亲为。《应县报》为宣传县委、县政府的中心工作,促进应县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在我的印象中,还培养出了不少人才。《山西日报》记者马占富,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广,县文联主席温晋华,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仙文等等一大批爱好文字写作的人都是通过《应县报》走向了更高的层次。
岁月不饶人,时光催人老。马老师也在逐渐变老。2006年,由于年龄原因,马进纲离开了《应县报》的领导岗位,让位给了年富力强、才气过人的原县农业局局长张恩仕。
年届古稀,本来可以享受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了。可是,马进纲还想为县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事。于是,一份《塔乡儿女》杂志应运而生。
杂志社运行更为艰难,好多年来一直借用大同市一家单位的民房办公,条件十分简陋。办刊经费大多来自于老乡的资助,编务和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是义务帮忙的热心老乡。身边的人都被马进纲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所感染,心甘情愿地为《塔乡儿女》做事。身为《山西日报》副总编辑的儿子和《山西农民报》副总编辑的儿媳妇,在马老师的感召下,也加入了《塔乡儿女》编辑队伍之中。有意无意间使《塔乡儿女》的办刊水平提升了几个档次。我看了一下今年第二期是总第72期。70多期杂志的工作量有多大,需要一个耄耋老人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?我们无法想象。这也许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追求。
马进纲办报办刊热情似火,人们有什么难题找到他也会倾尽全力。记得有一年,田仁乳业董事长赵田仁给我打电话说,有件事急需找呼和浩特市的熟人解决。我立即联系了马主编,他二话没说,让我们去大同接他,一起赶往呼和浩特市。马主编找到了一位老乡,很快使这件比较缠手的事得到了妥善处理。
我和马进纲相识于应县县委宣传部,在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文章写得好。我毕业后,分配到了县畜牧局,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稿子,投出去几篇没有一篇见报。心想,可能是自己名气不大的缘故。一次,写了一篇以原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王福功为主人公的稿子——《部长刻苦学技术》,前面加了马进纲的名字。不久,《雁北报》头版刊发了。看到报上的稿子,既高兴,又不安。因为,我没有和马老师打招呼就加了他的名字。多少年以后,和马老师谈起这件事,他印象不是太深。倒是原朔州日报社社长齐凤翔还记忆犹新。他说,这篇稿子是我编的,不是因为你加了马进纲的名字而给你编发,稿子本来写得不错。
不管是什么原因,这是我发的第一篇稿子。就是因为我一年时间在《雁北报》发了十几篇稿件,于1981年底调到宣传部通讯科。当时,宣传部部长张伟,通讯科长孙贵,马进纲是副科长。在张部长的领导下,部里工作蒸蒸日上,井井有条。当时的工作环境,大家和谐相处的气氛令我终生难忘。
在这期间,我对马进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业务能力特别强。一次,他领着我去东辉耀村下乡。晚上,和我边聊天边写作,连草稿也没有打,一气呵成。一篇写林业局局长的稿子不久就上了《山西日报》的头版头条。当了20多年山西日报记者,我深知《山西日报》的头版头条本报记者也很难发。
直到退休之后,我才领悟到:一个人不在于当多大的官,而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多少有益于人民的事。马进纲没有当多大的官,但是,他为家乡父老乡亲做的事,超过了很多人。
今年7月初,马占富说马老师病了。我和他说,你有空咱们一起回去看看他老人家。
7月9日,我和占富相约看望了马老师。在简陋的平房里,我看到马老师的茶几上还放着打印的文字材料,可能他在病中还在工作。马老师说:“我没有在搓麻将、打扑克上耗费过半天时光,只想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我们和马老师一起坐了半个多小时,临走时他还硬要送我们,被我们硬拦了回去。当时感觉老人的精神状态还可以,两三年内应该没问题。
临走时说好了,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望他。可是,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,马老突然走了。离开了爱他的亲人朋友,离开了他眷恋的美好世界。
这一天是8月3日——朔州大地,淅淅沥沥地下着不大不小的雨,如泣如诉,一刻也不愿意停息,仿佛一边在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离去而哭泣,一边在向人们诉说这位老人的所作所为。
马老,您太累了,应该休息一下了。
马老,您放心吧!有您给铺好的路,后人会沿着您的足迹,把《应县报》和《塔乡儿女》办得更好。
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当拿到《塔乡儿女》之后,总是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。
依靠一己之力创办一张县报和一份县级综合刊物,在全省我不敢说是绝无仅有,但肯定为数不多。马进纲做到了。
马进纲因为当过老师,从政之后,好多人还习惯称呼他:“马老师。”有不少厅处级领导都是他的学生。
德高则望重,行端令人敬。多年来,接触过马进纲的人都对他特别尊重。有几位省级领导和部队的将军都和他有联系。
他为一位将军寻找好心人的故事被传为佳话。几十年前这位将军还在家乡上学。他步行进城,路上肚子突然痛了起来,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发现后把他送到了医院。他说曾经委托《塔乡儿女》主编马进纲给寻找,未能如愿。这位将军正好是我的同学,他也曾经和我谈起过此事。为了了却将军的心愿,我在2021年6月7日《应县报》头版刊发了《一位高级将领寻找好人陈义》的短文。在《塔乡儿女》今年第一期上,我看到了社长贺诚的文章《为了塔乡儿女》,才知道马进纲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查访,终于找到了这位骑车人。将军得知这个结果后,十分高兴。
说是县报县刊,其实并没有正常的人员编制和财政拨款,运作困难可想而知。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很难坚持下去。那是1996年的一天,我已经调到山西日报社,马进纲又回到县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。几个人在马部长办公室闲聊,说起应县应该办一份报纸,马部长最适合做这个事。
好多思路只是想想而已,要变成现实有诸多难题。也许马进纲就是这种能够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人。没过多长时间,我突然看到了白纸黑字的《应县报》,大为震撼。之后,马部长全身心投入到了办报之中,总编、记者、校对、发行,几乎都要亲力亲为。《应县报》为宣传县委、县政府的中心工作,促进应县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在我的印象中,还培养出了不少人才。《山西日报》记者马占富,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广,县文联主席温晋华,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仙文等等一大批爱好文字写作的人都是通过《应县报》走向了更高的层次。
岁月不饶人,时光催人老。马老师也在逐渐变老。2006年,由于年龄原因,马进纲离开了《应县报》的领导岗位,让位给了年富力强、才气过人的原县农业局局长张恩仕。
年届古稀,本来可以享受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了。可是,马进纲还想为县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事。于是,一份《塔乡儿女》杂志应运而生。
杂志社运行更为艰难,好多年来一直借用大同市一家单位的民房办公,条件十分简陋。办刊经费大多来自于老乡的资助,编务和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是义务帮忙的热心老乡。身边的人都被马进纲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所感染,心甘情愿地为《塔乡儿女》做事。身为《山西日报》副总编辑的儿子和《山西农民报》副总编辑的儿媳妇,在马老师的感召下,也加入了《塔乡儿女》编辑队伍之中。有意无意间使《塔乡儿女》的办刊水平提升了几个档次。我看了一下今年第二期是总第72期。70多期杂志的工作量有多大,需要一个耄耋老人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?我们无法想象。这也许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和追求。
马进纲办报办刊热情似火,人们有什么难题找到他也会倾尽全力。记得有一年,田仁乳业董事长赵田仁给我打电话说,有件事急需找呼和浩特市的熟人解决。我立即联系了马主编,他二话没说,让我们去大同接他,一起赶往呼和浩特市。马主编找到了一位老乡,很快使这件比较缠手的事得到了妥善处理。
我和马进纲相识于应县县委宣传部,在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文章写得好。我毕业后,分配到了县畜牧局,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稿子,投出去几篇没有一篇见报。心想,可能是自己名气不大的缘故。一次,写了一篇以原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王福功为主人公的稿子——《部长刻苦学技术》,前面加了马进纲的名字。不久,《雁北报》头版刊发了。看到报上的稿子,既高兴,又不安。因为,我没有和马老师打招呼就加了他的名字。多少年以后,和马老师谈起这件事,他印象不是太深。倒是原朔州日报社社长齐凤翔还记忆犹新。他说,这篇稿子是我编的,不是因为你加了马进纲的名字而给你编发,稿子本来写得不错。
不管是什么原因,这是我发的第一篇稿子。就是因为我一年时间在《雁北报》发了十几篇稿件,于1981年底调到宣传部通讯科。当时,宣传部部长张伟,通讯科长孙贵,马进纲是副科长。在张部长的领导下,部里工作蒸蒸日上,井井有条。当时的工作环境,大家和谐相处的气氛令我终生难忘。
在这期间,我对马进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业务能力特别强。一次,他领着我去东辉耀村下乡。晚上,和我边聊天边写作,连草稿也没有打,一气呵成。一篇写林业局局长的稿子不久就上了《山西日报》的头版头条。当了20多年山西日报记者,我深知《山西日报》的头版头条本报记者也很难发。
直到退休之后,我才领悟到:一个人不在于当多大的官,而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多少有益于人民的事。马进纲没有当多大的官,但是,他为家乡父老乡亲做的事,超过了很多人。
今年7月初,马占富说马老师病了。我和他说,你有空咱们一起回去看看他老人家。
7月9日,我和占富相约看望了马老师。在简陋的平房里,我看到马老师的茶几上还放着打印的文字材料,可能他在病中还在工作。马老师说:“我没有在搓麻将、打扑克上耗费过半天时光,只想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我们和马老师一起坐了半个多小时,临走时他还硬要送我们,被我们硬拦了回去。当时感觉老人的精神状态还可以,两三年内应该没问题。
临走时说好了,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望他。可是,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,马老突然走了。离开了爱他的亲人朋友,离开了他眷恋的美好世界。
这一天是8月3日——朔州大地,淅淅沥沥地下着不大不小的雨,如泣如诉,一刻也不愿意停息,仿佛一边在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离去而哭泣,一边在向人们诉说这位老人的所作所为。
马老,您太累了,应该休息一下了。
马老,您放心吧!有您给铺好的路,后人会沿着您的足迹,把《应县报》和《塔乡儿女》办得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