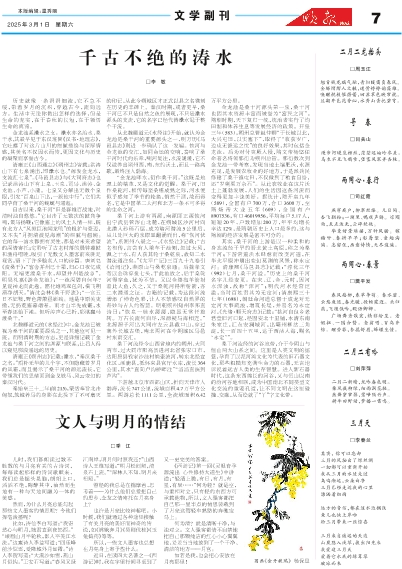千古不绝的涛水
文章字数:2462
历史就像一条涓涓细流,它不急不缓,带着岁月的沉积,穿越古今,流向远方。生活中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,但是生命的充实,在于春秋的长短,在于领悟生命的真谛。
金龙池系㶟水之支。㶟水亦名治水、桑干水,其最早见于东汉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,它吐露了对这片山川的细腻描绘与深厚情感,其美名不仅因水而传,更因文化与历史的凝聚而享誉古今。
清雍正《山西通志》《朔州志》皆载:洪涛山下有七泉涌出,即㶟水也。“源发金龙水,支流汇七泉”。《马邑县志》与《大同府志》也记录洪涛山下有上泉、玉泉、司马、洪涛、金龙池、小芦、小蒲。七泉又分解出无数个泉眼,引发“百泉山下出,一派地中行”,它们共同孕育了桑干河的蜿蜒与逶迤。
自古以来,桑干河“旧是群雄百战地,时清时浊自悠悠。”它目击了无数次的鼓角争鸣,策马扬鞭;它像塞上的风土人情一样,既有北方人“风掀巨浪闻龙吼”的粗犷与豪迈,又不失“月拥清波见海潮”的细腻与温婉。它的每一滴水都拥有灵性,都是对未来希望的深情寄托;它聆听了古老村落的晨钟暮鼓和渔舟唱晚,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驻足观赏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唐刘皂《渡桑干》:“客舍并州已十霜,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更渡桑干水,却望并州是故乡”。明吴礼嘉《游金龙池》:“一池深碧自何年?见说神龙向此卷。愿化雄鸡双包剑,横飞朔漠净胡天。”清沈会林《桑干野涨》:“一官五日不征鞍,野色萧萧昼影残。地是中原关吏撤,无扔荒塞暮烟寒。雨才山半先成霰,水至春还始下滩。但听涛声心已折,那堪羸马渡桑干。”
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,金龙池已被视为桑干河的重要源头之一,其地位可见一斑。而明清时期的方志,更是详细记载了金龙池与桑干河之间的渊源与联系,让后人得以窥见那段遥远的历史。
清雍正《朔州志》记载:㶟水,“秦汉桑干之名。”质朴无华的几个字,不但隐藏着岁月的风霜,而且揭示了桑干河的源远流长,它带领我们的思绪回到金戈铁马、风云变幻的秦汉时代。
秦始皇三十二年(前215),蒙恬奉旨北击匈奴,筑城养马的身影在此投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,从此今朔城区才正式以县之名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秦汉时期,或者更早,桑干河已不只是自然之色的展现,不只是㶟水源头的支流,它的名字已经代替㶟水冠于整个干流。
从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开始,就认为金龙池是桑干河的重要源头之一,明万历《马邑县志》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发端。恢河与金龙池的交汇,如同命运的交响,奏响了桑干河时代的乐章,喇河复注,水流湲湲,它不仅滋养出朔州西、南、东的沃土,而且一路高歌,最终注入渤海。
“金龙池畔水,衍作桑干河。”这既是地理上的鼎革,又是文化的觉醒。桑干河,旧作桑乾河,相传每至桑椹成熟之际,河水便似乎感知了季节的轮换,悄然干涸,故而得名,它是中国第二大河和北方一条不可多得的生命之河。
桑干河上游有两源,南源即正源恢河出宁武县管涔山北麓,在朔城区沙河村向北潜入砂砾石层,成为暗河潜流5公里后,从几处巨大的泉眼里翻涌而出,称“恢河伏流”,系朔州八景之一。《水经注》记载:“古老相传,言尝有人乘车于池侧,忽过大风,飘之于水,有人获其轮于桑乾泉,故知二水潜流通注矣。”《太平广记》三百九十九卷引《洽闻记》,燕原山与桑乾泉通。后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鱼七头,于此池放之,后于桑乾河得穿鱼,犹为不信。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,久之,又于桑乾河得所射箭,亦二水潜通之证。古籍的记载,为这段河流增添了神奇色彩,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界的奇妙与古人的智慧。明朝朔州知州李邦直诗曰:“恢泉一脉水潺潺,隐显无常任旋转。万古长流何自尽,深源疑与海相连。”北源源子河出大同市左云县截口山,穿过塞外长城古堡,南北两河在今朔城区马邑村东南交汇。
桑干河流经今山西省境内的朔州、大同两市,过大同市阳高县进河北省张家口市,达阳原县钱家沙洼村纳壶流河,转东北经宣化区、涿鹿县,抵怀来县官厅水库,流长364公里,其水“直向卢沟桥畔注”“滔滔直演到芦沟”。
下游越北京市西部山区,折向天津市入渤海,流长747公里,流域面积4.7万平方公里。两游总长1111公里,全流域面积6.42万平方公里。
金龙池是桑干河源头第一泉,桑干河也因其水资源丰富而被誉为“富民之河”。隋朝时期,天下复归一统,统治者实行了均田制和休养生息等发展经济的政策。开皇三年(583),朔州总管赵仲卿“于长城以北,大兴屯田,以实塞下”,取得了“收获岁广,边戍无馈运之忧”的良好效果,其时包括金龙池。后为对付突厥入侵,隋文帝杨坚任命著名将领郭衍为朔州总管。郭衍数次到金龙池一带考察,发现当地土壤肥沃,水源充足,是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,于是派兵民修建了桑干镇屯田,不仅做到了粮食自给,还“岁剩粟万余石”。从此农牧业在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,人们的生活因这条河流而变得更加丰饶美好。据统计,隋开皇九年(589),全国有户700万,合口3600万,至
隋 炀 帝 大 业 五 年(609),全 国 有 户8907536,有口46019956,平均每户5.17人,短短20年,户数增加200万,年平均增长率达12%,是隋朝历史上人口最多的,这与隋朝的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。
其实,桑干河的上游是以一种柔和的身态流经干旱的晋北黄土高原,称之为桑干河;下游常遭洪水肆虐而改变河道,在华北平原冲刷出变幻莫测的风景,称永定河。清康熙《马邑县志》记载:“淳化三年(992)七月,桑干河溢。”历史上的桑干河名字几经变更。在宋、辽、金、元时,因河水浑浊,故称“浑河”;明代河水经常泛滥,当时百姓责其为无定河;清康熙三十七年(1698),朝廷命河道总督于成龙对无定河大事疏浚,增筑长堤,并易名为永定河。《光绪·顺天府志》记载:“挑河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,经固安北十里铺,永清东南朱家庄,汇东安澜城河,出霸州柳岔三角淀,长一百四十五里,达于西沽入海,赐名‘永定’”。
桑干河流经的河谷地带,介于今阴山与恒山两大山系之间。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摇篮,孕育了以泥河湾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,那些粗糙却充满生命力的石器,无言地诉说着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。进入新石器时代,这条东西绵长的河谷,又与恒山以南的汾河谷地相联,成为中国南北不同类型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,让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、交融,从而绘就了“丫”字文化带。
金龙池系㶟水之支。㶟水亦名治水、桑干水,其最早见于东汉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,它吐露了对这片山川的细腻描绘与深厚情感,其美名不仅因水而传,更因文化与历史的凝聚而享誉古今。
清雍正《山西通志》《朔州志》皆载:洪涛山下有七泉涌出,即㶟水也。“源发金龙水,支流汇七泉”。《马邑县志》与《大同府志》也记录洪涛山下有上泉、玉泉、司马、洪涛、金龙池、小芦、小蒲。七泉又分解出无数个泉眼,引发“百泉山下出,一派地中行”,它们共同孕育了桑干河的蜿蜒与逶迤。
自古以来,桑干河“旧是群雄百战地,时清时浊自悠悠。”它目击了无数次的鼓角争鸣,策马扬鞭;它像塞上的风土人情一样,既有北方人“风掀巨浪闻龙吼”的粗犷与豪迈,又不失“月拥清波见海潮”的细腻与温婉。它的每一滴水都拥有灵性,都是对未来希望的深情寄托;它聆听了古老村落的晨钟暮鼓和渔舟唱晚,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驻足观赏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唐刘皂《渡桑干》:“客舍并州已十霜,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更渡桑干水,却望并州是故乡”。明吴礼嘉《游金龙池》:“一池深碧自何年?见说神龙向此卷。愿化雄鸡双包剑,横飞朔漠净胡天。”清沈会林《桑干野涨》:“一官五日不征鞍,野色萧萧昼影残。地是中原关吏撤,无扔荒塞暮烟寒。雨才山半先成霰,水至春还始下滩。但听涛声心已折,那堪羸马渡桑干。”
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,金龙池已被视为桑干河的重要源头之一,其地位可见一斑。而明清时期的方志,更是详细记载了金龙池与桑干河之间的渊源与联系,让后人得以窥见那段遥远的历史。
清雍正《朔州志》记载:㶟水,“秦汉桑干之名。”质朴无华的几个字,不但隐藏着岁月的风霜,而且揭示了桑干河的源远流长,它带领我们的思绪回到金戈铁马、风云变幻的秦汉时代。
秦始皇三十二年(前215),蒙恬奉旨北击匈奴,筑城养马的身影在此投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,从此今朔城区才正式以县之名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秦汉时期,或者更早,桑干河已不只是自然之色的展现,不只是㶟水源头的支流,它的名字已经代替㶟水冠于整个干流。
从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开始,就认为金龙池是桑干河的重要源头之一,明万历《马邑县志》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发端。恢河与金龙池的交汇,如同命运的交响,奏响了桑干河时代的乐章,喇河复注,水流湲湲,它不仅滋养出朔州西、南、东的沃土,而且一路高歌,最终注入渤海。
“金龙池畔水,衍作桑干河。”这既是地理上的鼎革,又是文化的觉醒。桑干河,旧作桑乾河,相传每至桑椹成熟之际,河水便似乎感知了季节的轮换,悄然干涸,故而得名,它是中国第二大河和北方一条不可多得的生命之河。
桑干河上游有两源,南源即正源恢河出宁武县管涔山北麓,在朔城区沙河村向北潜入砂砾石层,成为暗河潜流5公里后,从几处巨大的泉眼里翻涌而出,称“恢河伏流”,系朔州八景之一。《水经注》记载:“古老相传,言尝有人乘车于池侧,忽过大风,飘之于水,有人获其轮于桑乾泉,故知二水潜流通注矣。”《太平广记》三百九十九卷引《洽闻记》,燕原山与桑乾泉通。后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鱼七头,于此池放之,后于桑乾河得穿鱼,犹为不信。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,久之,又于桑乾河得所射箭,亦二水潜通之证。古籍的记载,为这段河流增添了神奇色彩,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界的奇妙与古人的智慧。明朝朔州知州李邦直诗曰:“恢泉一脉水潺潺,隐显无常任旋转。万古长流何自尽,深源疑与海相连。”北源源子河出大同市左云县截口山,穿过塞外长城古堡,南北两河在今朔城区马邑村东南交汇。
桑干河流经今山西省境内的朔州、大同两市,过大同市阳高县进河北省张家口市,达阳原县钱家沙洼村纳壶流河,转东北经宣化区、涿鹿县,抵怀来县官厅水库,流长364公里,其水“直向卢沟桥畔注”“滔滔直演到芦沟”。
下游越北京市西部山区,折向天津市入渤海,流长747公里,流域面积4.7万平方公里。两游总长1111公里,全流域面积6.42万平方公里。
金龙池是桑干河源头第一泉,桑干河也因其水资源丰富而被誉为“富民之河”。隋朝时期,天下复归一统,统治者实行了均田制和休养生息等发展经济的政策。开皇三年(583),朔州总管赵仲卿“于长城以北,大兴屯田,以实塞下”,取得了“收获岁广,边戍无馈运之忧”的良好效果,其时包括金龙池。后为对付突厥入侵,隋文帝杨坚任命著名将领郭衍为朔州总管。郭衍数次到金龙池一带考察,发现当地土壤肥沃,水源充足,是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,于是派兵民修建了桑干镇屯田,不仅做到了粮食自给,还“岁剩粟万余石”。从此农牧业在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,人们的生活因这条河流而变得更加丰饶美好。据统计,隋开皇九年(589),全国有户700万,合口3600万,至
隋 炀 帝 大 业 五 年(609),全 国 有 户8907536,有口46019956,平均每户5.17人,短短20年,户数增加200万,年平均增长率达12%,是隋朝历史上人口最多的,这与隋朝的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。
其实,桑干河的上游是以一种柔和的身态流经干旱的晋北黄土高原,称之为桑干河;下游常遭洪水肆虐而改变河道,在华北平原冲刷出变幻莫测的风景,称永定河。清康熙《马邑县志》记载:“淳化三年(992)七月,桑干河溢。”历史上的桑干河名字几经变更。在宋、辽、金、元时,因河水浑浊,故称“浑河”;明代河水经常泛滥,当时百姓责其为无定河;清康熙三十七年(1698),朝廷命河道总督于成龙对无定河大事疏浚,增筑长堤,并易名为永定河。《光绪·顺天府志》记载:“挑河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,经固安北十里铺,永清东南朱家庄,汇东安澜城河,出霸州柳岔三角淀,长一百四十五里,达于西沽入海,赐名‘永定’”。
桑干河流经的河谷地带,介于今阴山与恒山两大山系之间。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摇篮,孕育了以泥河湾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,那些粗糙却充满生命力的石器,无言地诉说着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。进入新石器时代,这条东西绵长的河谷,又与恒山以南的汾河谷地相联,成为中国南北不同类型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,让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、交融,从而绘就了“丫”字文化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