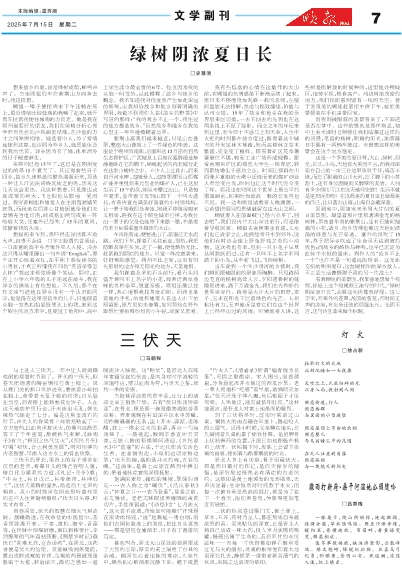三 伏 天
文章字数:1613
马上进入三伏天,一年中让人最烦躁难耐的烦暑时节到了。晋北的三伏天,似苍天把烧透的陶窑倒扣在黄土塬上。风从雁门关的豁口里挤进来,裹挟着沙砾拍在脸上,竟带着火星子般的灼烫;日头悬在当空,沥青路上能烙熟莜面饼子。人在这天地熔炉里行走,汗未渗出毛孔,倒先被热气舔走了七分。偏是这焦金流石的时节,晋北人的脊梁骨上却悄然贴起了一方方膏药,以血肉承接伏火,仿佛与这酷烈签下了千年密契,静候秋气来解。《淮南子》有言:“积阳之热气生火”,《四民月令》叮嘱“初伏,合止利黄连圆”,阴阳相搏的古老智慧,早渗入这方水土的骨血纹路。
三伏天的晋北,梁峁上的谷子垂首如沉思的老者,将毒日头的锋芒吞咽入腹,暗自化为灌浆的力道。《礼记·月令》载:“中央土,其日戊己,其帝黄帝,其神后土”,这伏天蒸腾的湿热,恰是后土无声的哺育。我小的时候常在田地里听着村里的庄户人拄着锄柄慨叹:“伏天日头毒,籽实才有骨。”
街巷深处,伏天的智慧在烟火气里流转。晨曦微透,在我单位的中医馆中,苦香便弥漫开来。干姜、黄柏、细辛、香薷等,在研钵中细细研磨,调以新榨姜汁,辛烈醇厚的气味直钻肺腑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伏日“其毒尤烈,宜合汤药”,在晋北,这药香便是伏天的信使。孩童被唤到条凳前,露出或胖或瘦的脊背,乌褐的药膏被郑重敷贴于大椎、肺俞诸穴,微灼之感如一道暖流注入腠理。这“贴伏”,是晋北人向陈年寒痼发起的伏击,是肉身对时序流转的深邃呼应,便以血肉为符,与炎天立誓,预约一季的安康。
当街巷浮动着药草辛香,灶台上的清凉文章正悄然开场。古有“伏日作汤饼辟恶”,在晋北,便是那一碗澄澈筋道的苦荞凉粉。荞麦魂魄在村里深井凉水中苏醒,切作颤巍巍的玉条,浇上芥末、蒜泥、老陈醋,放上一绺汆过水的韭菜,再点一勺油泼辣子。一筷挑起,酸冽辛香直冲天灵盖,五脏六腑的郁燥瞬间溃退。《齐民要术》中“菹齑”的古法,于此化作舌尖活色生香。在商铺街边,小贩们边切凉粉边笑:“伏天的碗,盛的是井水的魂,五谷的魄。”这滋味,是黄土高原在酷烈中捧出的、带着地脉凉意的深情抚慰。
饱满的麦粒、赭红的辣椒、翠绿的西瓜……农人称之为“曝伏”。《吕氏春秋》云:“仲夏之月……农乃登黍”,登黍之前,必先曝伏。老把式眯眼望着曝晒的黄芪切片,手捻须髯道:“《诗经》言‘七月流火’,这火若不流透,药性如何能凝?”汗珠砸在滚烫的场院,“滋”地腾起一缕白烟,而他们古铜色脸庞上的笑纹,却比日头更亮——那是望见仓廪渐丰、日子有了着落的笃定。
暮色四合,晋北大山深处的窑洞便成了天然的玉琮,厚实的黄土隔绝了白昼的余威。幽深处沁着地脉的寒凉,人坐其中,燥热的心肺渐渐沉静下来。檐下或置一“竹夫人”,《清嘉录》所谓“编青篾为长笼”,可拥之取微凉。家人围坐,摇着蒲扇,分食晨起汲井水镇过的西瓜沙果。老一辈人用烟杆“吧嗒”着旱烟,烟锅明灭如星:“伏天汗珠子摔八瓣,秋后粮囤子才压弯梁。人哄地皮,地皮就饿你肚皮。”这朴拙箴言,是晋北人对黄土地最深的敬畏。
到了三伏将尽时,雷雨时常滚过山梁。铜钱大的雨点砸在田垄上,腾起呛人的土腥气。记得小时候,父亲蹲在地头,长久凝视着久渴的黍子痛饮甘霖。他肩胛骨上伏贴膏药的位置,汗渍已如地图般在粗布上洇开。伏帖揭下时,皮肤上会留下淡褐的圆痕,铭刻着与酷暑鏖战的时光。
晋北人身上有伏痕,骨子里藏伏火。那是烈日锻打的印记,是向天挣岁的倔强,是深信熬过极热必有清凉的古老信约。这烙印是黄土地颁发的无形勋章,无声诉说着:生命纵然时时煎熬于水火,但每一次俯身承受热浪的锻打,都是为了在下一个春天,能向着苍穹,伸展得更加笔直而硬朗。
三伏的热风卷过雁门关,黄土塬上,草木、五谷、药材乃至人,都在熬炼自身最浓烈的香。原来贴伏的深意,正是晋北人将自己活成一味大药,投入岁月蒸腾的陶罐,慢煎出属于生命的、苦后回甘的永恒滋味——当每一寸伏脊都如碑石般承受过光与火的凿刻,灵魂的根须便向着大地更深处扎去,静候第一缕带着新谷清气的秋风,来揭去这滚烫的烙印。
三伏天的晋北,梁峁上的谷子垂首如沉思的老者,将毒日头的锋芒吞咽入腹,暗自化为灌浆的力道。《礼记·月令》载:“中央土,其日戊己,其帝黄帝,其神后土”,这伏天蒸腾的湿热,恰是后土无声的哺育。我小的时候常在田地里听着村里的庄户人拄着锄柄慨叹:“伏天日头毒,籽实才有骨。”
街巷深处,伏天的智慧在烟火气里流转。晨曦微透,在我单位的中医馆中,苦香便弥漫开来。干姜、黄柏、细辛、香薷等,在研钵中细细研磨,调以新榨姜汁,辛烈醇厚的气味直钻肺腑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伏日“其毒尤烈,宜合汤药”,在晋北,这药香便是伏天的信使。孩童被唤到条凳前,露出或胖或瘦的脊背,乌褐的药膏被郑重敷贴于大椎、肺俞诸穴,微灼之感如一道暖流注入腠理。这“贴伏”,是晋北人向陈年寒痼发起的伏击,是肉身对时序流转的深邃呼应,便以血肉为符,与炎天立誓,预约一季的安康。
当街巷浮动着药草辛香,灶台上的清凉文章正悄然开场。古有“伏日作汤饼辟恶”,在晋北,便是那一碗澄澈筋道的苦荞凉粉。荞麦魂魄在村里深井凉水中苏醒,切作颤巍巍的玉条,浇上芥末、蒜泥、老陈醋,放上一绺汆过水的韭菜,再点一勺油泼辣子。一筷挑起,酸冽辛香直冲天灵盖,五脏六腑的郁燥瞬间溃退。《齐民要术》中“菹齑”的古法,于此化作舌尖活色生香。在商铺街边,小贩们边切凉粉边笑:“伏天的碗,盛的是井水的魂,五谷的魄。”这滋味,是黄土高原在酷烈中捧出的、带着地脉凉意的深情抚慰。
饱满的麦粒、赭红的辣椒、翠绿的西瓜……农人称之为“曝伏”。《吕氏春秋》云:“仲夏之月……农乃登黍”,登黍之前,必先曝伏。老把式眯眼望着曝晒的黄芪切片,手捻须髯道:“《诗经》言‘七月流火’,这火若不流透,药性如何能凝?”汗珠砸在滚烫的场院,“滋”地腾起一缕白烟,而他们古铜色脸庞上的笑纹,却比日头更亮——那是望见仓廪渐丰、日子有了着落的笃定。
暮色四合,晋北大山深处的窑洞便成了天然的玉琮,厚实的黄土隔绝了白昼的余威。幽深处沁着地脉的寒凉,人坐其中,燥热的心肺渐渐沉静下来。檐下或置一“竹夫人”,《清嘉录》所谓“编青篾为长笼”,可拥之取微凉。家人围坐,摇着蒲扇,分食晨起汲井水镇过的西瓜沙果。老一辈人用烟杆“吧嗒”着旱烟,烟锅明灭如星:“伏天汗珠子摔八瓣,秋后粮囤子才压弯梁。人哄地皮,地皮就饿你肚皮。”这朴拙箴言,是晋北人对黄土地最深的敬畏。
到了三伏将尽时,雷雨时常滚过山梁。铜钱大的雨点砸在田垄上,腾起呛人的土腥气。记得小时候,父亲蹲在地头,长久凝视着久渴的黍子痛饮甘霖。他肩胛骨上伏贴膏药的位置,汗渍已如地图般在粗布上洇开。伏帖揭下时,皮肤上会留下淡褐的圆痕,铭刻着与酷暑鏖战的时光。
晋北人身上有伏痕,骨子里藏伏火。那是烈日锻打的印记,是向天挣岁的倔强,是深信熬过极热必有清凉的古老信约。这烙印是黄土地颁发的无形勋章,无声诉说着:生命纵然时时煎熬于水火,但每一次俯身承受热浪的锻打,都是为了在下一个春天,能向着苍穹,伸展得更加笔直而硬朗。
三伏的热风卷过雁门关,黄土塬上,草木、五谷、药材乃至人,都在熬炼自身最浓烈的香。原来贴伏的深意,正是晋北人将自己活成一味大药,投入岁月蒸腾的陶罐,慢煎出属于生命的、苦后回甘的永恒滋味——当每一寸伏脊都如碑石般承受过光与火的凿刻,灵魂的根须便向着大地更深处扎去,静候第一缕带着新谷清气的秋风,来揭去这滚烫的烙印。